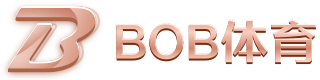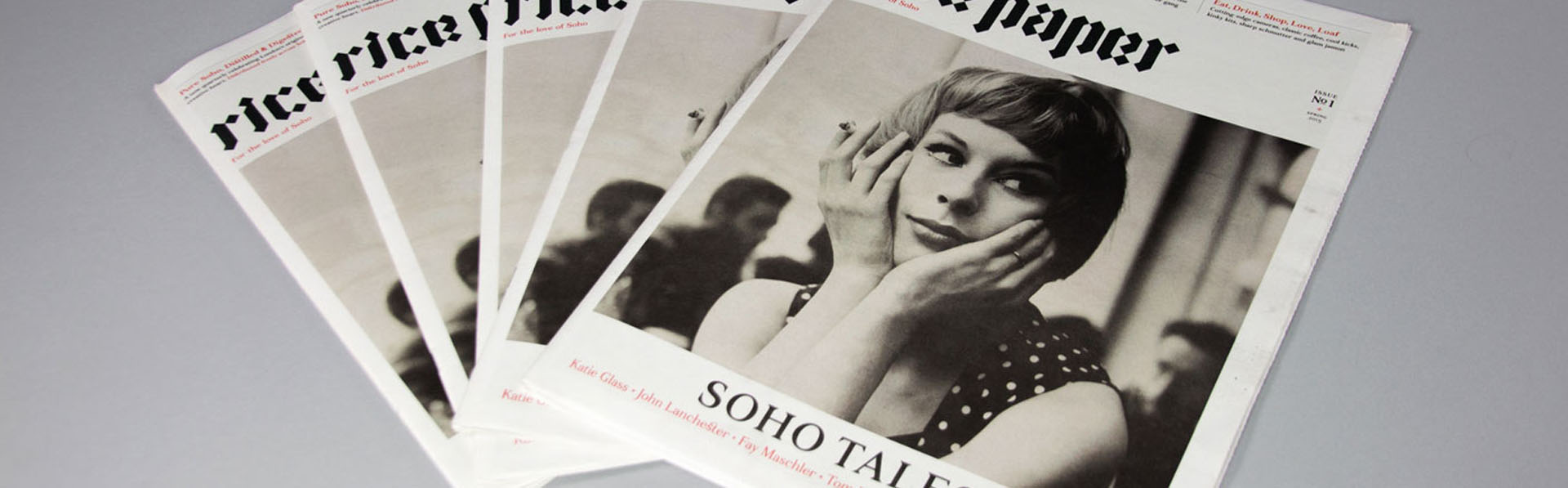BOB综合体育2023年,在汹涌的时代浪潮中,人们尝试与不安、焦虑和迷茫共存,立住脚跟、尽力向上,重新构筑自己的生活。
在中国,一群纪录片创作者找到了契机,去记录下一群普通人积攒能量的 2023 年。乐队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,舞台上的灯光熄灭,银幕亮起。创作团队努力多时的成果,终于在2023蔚来日(NIO Day 2023)的西安奥体中心现场首次展映。故事里,人们像世界的种子,兀自生长。
吃过早饭从宾馆里出来,青藏高原上的天空仍然不见光亮,如同黑夜。停在空地上的车子,前窗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。为了安全上路,潘国义和邱荷芬夫妇俩一边吃力地喘气,一边拿小铲子将车窗上的冰一点点刮掉,又钻进车里将空调打开,才重新拥有前窗的视野。
空旷的公路上,少有车辆驶过。太阳从远处的地平线缓缓升起,蓝天也逐渐澄澈。
潘国义今年已经74岁,这是他第三次进藏,距离上一次已经过了二十余年。五十年前,他参与格尔木至输油管线的建设,从长三角的平原地区来到高原上。在青藏线上,一呆就是十几年。那段和战友们并肩奋斗的日子始终是他最为珍藏的回忆。人至暮年,越发容易想起过去的岁月,趁着身体还算硬朗,他想和妻子一起回到高原上,再看一看过去挥洒过青春的地方。
这个愿望在潘国义心中埋藏已久,却始终未能成行。原本去年就有打算,也因故耽搁。终于在今年,老两口找到了机会。
眼看着一年即将过去,纪录片《风味人间》制作人朱乐贤希望能有一部作品,记录这个剧变的时代下普通人的变化。在他看来,从去年到今年,人们的生活在一番波折后逐渐复苏,普通人作为时代的参与者,他们内在与外在状态的变化是这个时代的缩影。于是,他担任监制,开始寻觅伙伴。曾执导纪录片《生活万岁》的导演程工,喜欢观察和记录人的复杂性,在朱乐贤的邀约下,他接下了这份工作。
想在年底给人们带来慰藉与鼓励,主创团队选择将2023蔚来日(NIO Day 2023)的主题“向上”也作为纪录片的主题。9月初,他们向全网发布征集问卷,经过层层筛选,最终敲定了横跨各个年龄层和行业的八位拍摄对象。潘国义就是其中之一,从他提交的信息中,朱乐贤看到了人至暮年仍然留有的勇气与激情。他和程工导演想要这对年迈的夫妻实现愿望。
出发前,潘国义在网上浏览了许多人分享的游记,自己筛选制作了一份路书。即使做了充足的准备,出发当天,潘国义睡得并不好,大脑被各种各样的思虑塞满。早已做好计划的路线盘绕在他脑海里,可能遇到的困难也涌现在想象中。他早早醒来,再难睡去,和妻子一起五点多就起了床,六点整理好行装,就开着车出发了。
从长江千年前的入海口江苏江阴,一路逆流而上,到达长江源头沱沱河所在的唐古拉山口。夫妻俩路上花了十几天的时间。
到格尔木昆仑管道附近时,天已经快黑了,气温也急剧下降。曾经被评为“优秀工程”的管道静静矗立在风中,数十年如一日,担当着运输油气的功能。如今潘国义苍老了,这段他曾参与修造的管道,表面也显现出历经风雨的沧桑。
这是潘国义所在的部队修筑的第一段管道。管道选址在一处40多米高的悬崖峭壁旁。五十多年前没有吊车,一根十一二米的管子要靠十几个人抬上去。风吹日晒,潘国义脸上起了皮,像鱼鳞一样一片接一片。回忆着过去,潘国义和邱荷芬在管道旁搭了一顶帐篷,暂时避风。躲在里面,他们就着保温壶里的热水,一点一点咽了几块馒头。
潘国义想起过去,邱荷芬也激动起来,说起了管道修筑时,这个家庭另一面的生活:“我在家里也苦的。”
生两个儿子的时候,潘国义都在青藏线上,无法回家。邱荷芬既要工作,又要拉扯孩子。通讯不发达,夫妻俩只能靠信件交流。就连孩子出生的消息,潘国义也是十几天后收到信才知道。后来邱荷芬因为工作调动,带着孩子来了格尔木,潘国义也很难从工程中抽身来分担家里的事务。潘国义为国家建设拼搏时,邱荷芬奋力撑起这个小家。
曾经的意气风发已不可追。再上高原,老两口随身带了血压计和降压药。从格尔木往上到唐古拉山,高原反应越发明显。他们头疼得睡不着觉,戴着输氧管,一晚也只能睡三四个小时。已经有两年不用吃降压药的潘国义,又一次拧开了熟悉的药瓶,取出几粒,放进嘴里,一口咽下。越靠近唐古拉山,温度越低,夫妻俩反复确认着彼此的情况,将带来的所有衣服都穿在了身上。
本片制片人宋晓晓印象最深的便是潘国义夫妻俩相互关心的方式。他们很少直白地讲出自己的担忧,总在温柔的拉锯和小小的拌嘴中关心彼此。
行驶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原公路上,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,潘国义试图劝说妻子邱荷芬一起去一趟海拔相近的珠峰营地:“这一生中不可能有第二次了,你回去之后,你是个吹牛人了。”邱荷芬说自己不喜欢吹牛,只喜欢两个人能互相多陪几年,她也担心出什么意外,回去不好向两个儿子交代。
可可西里的风猛烈地扑向夫妻俩,两人相互搀扶着蹒跚向前走。邱荷芬按住要飞走的帽子,念叨着:“我是冒着生命危险陪你来的啊。”
从唐古拉山口下来,老两口就开车去了医院。二人双双被高原反应击倒,半躺在床上吸氧。旅程中,宋晓晓多次收到导演组发来的信息,说老人高原反应严重,为了安全,随时要申请撤离。但夫妻两人坚持要完成这趟旅程,他们明白,这可能是他们这一生最后一次机会。
中秋节的前一天,潘国义和邱荷芬坐在的一座山上,看着夕阳,拆开了从家里背来的月饼。咽下月饼甜蜜的馅料,潘国义想起几十年前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乡愁。在给邱荷芬的信里,他曾写道:“我住长江头BOB综合体育,你住长江尾,从黑江水,寄出相思味。”从前的遗憾与思念,在暮年得以满足。
太阳隐入远处的山背,他忍不住吟诵: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”潘国义感怀当下生活的美好,却又遗憾人生尽头似乎已经近在眼前。
格尔木的烈士陵园里,整齐地躺着一块块方正的纪念碑。50年前为修建格尔木至的输油管线而牺牲的青年们,永久沉睡在这片土地,少有人来打破这里的宁静。9月,高原上的风已然凛冽。74岁的潘国义和妻子邱荷芬摘下帽子,站在碑前,一次次深深鞠躬。他们穿行在墓碑间,呢喃着熟悉的名字。
“我是你们的指导员,我来看你们的。”曾经二十几岁一起奋战的战友永远停留在正青春的年纪,潘国义却已然迟暮。帽子底下是花白且稀疏的头发,脸上是再难填平的沟壑。共同经历过那段艰苦的岁月,邱荷芬明白丈夫一句简单的低语背后,是怎样复杂的心绪。她站在丈夫身旁,团着纸拭去了眼角的眼泪。
从青藏高原回来以后,高原反应消退,潘国义的心中只剩满足。了却一桩夙愿,往后的晚年,他想带着这颗无法再发芽的种子,轻装上阵。回望过热血的青春,这份珍贵的回忆足以给予他力量,不带遗憾地向前看,和妻子健康、快乐地敲响人生的尾音。
为了2023年11月份的“蔚来杯”大学生方程式大赛,罗胤龙已经带着车队准备了整整一年。赛前,罗胤龙回家和父母吃过一次饭。饭桌上,父亲看着罗胤龙,问:“万一你在中途出了问题,你这一年就白费了是吧?”
罗胤龙低垂着眼睛,筷子在碗里挑动,没有正面回答,只淡淡回了一句:“失败是常态。”
从大一加入广东工业大学的车队,到去年年底开始担任队长,罗胤龙已经见证了车队的两场落败。2021年受疫情影响,只能办线上静态答辩赛,这本就是广东工业大学车队的弱项,对于二等奖的结果,罗胤龙并不感到奇怪。但去年动态赛的失败,给罗胤龙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打击。
比赛提前了两三个月,广东工业大学车队原本不打算参赛,但不想赛场经验断档,他们将前一年留下的,已经拆得四分五裂的旧车,重新组装好,登上了赛场。准备时间只有仓促的两个多月,没有充足的时间做测试,差点连车检都没通过。最终,去年的车因为电磁干扰,没有跑完动态赛,停在赛道中途,止步二等奖。
只要回到前八名,夺得一等奖,广东工业大学车队就能重回全国强队之列。在车队的众人眼中,今年是广东工业大学近三年来最有希望的一届。这一次设计的车在第一次试跑时就已经相对稳定,车手也是全国范围内的顶尖水平。
2017年,他还在读初三,偶然看到过广东工业大学的比赛视频。车顺滑地冲过终点线,主办方宣布广东工业大学获得第一名,队员们围在一起欢呼着冲上领奖台。罗胤龙当时已经在参加模型车比赛,他懂得当自己微小的努力与付出,能够被大家看见、认可,会是怎样的欣喜与激动。隔着屏幕,他感同身受。
进车队的三年,罗胤龙没有机会亲身在赛场上体会这种欣喜与满足。今年是他最后的机会,明年6月他就毕业了。
为了筹备这场赛事,罗胤龙和队员们耗尽心力,总在克服各种难题。为了省钱,他们还去学了几门技术,买原材料回来自己加工BOB综合体育。时间富余时,他们会接其他学校的加工订单,赚取经费。有时,一个零件就要2000块BOB综合体育。每个月里的两三天,罗胤龙靠着食堂一块钱的酱油饭生存。
工作室的黑板上,比赛倒计时的天数一天天减少,工作室亮到凌晨的灯也熄灭得越来越晚。
在工作室里,罗胤龙见过日出。今年10月,车子步入调试阶段,错综复杂的电路中掩藏着的小缺陷可能直接影响车子的发动,他们需要足够敏锐地将问题找出来,当天发现的问题必须当天解决,才不会影响第二天的其他测试。罗胤龙在工作室熬了整晚。躺在工作室的躺椅上,温热的光透过窗户落在他的眼皮上。起初,他以为是窗外的路灯,睁眼起身,走到门外,才发现太阳正升至半空,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一直到赛场上,突发状况仍然没有停止出现。从去年比赛后,罗胤龙就时常梦见,车子因为电控问题停在半路不动。比赛当天,罗胤龙又从一场梦境中醒来,打开手机,发现比赛举办地合肥当天的温度只有9度。他不由得和同房间的队友埋怨:“9度怎么比赛啊?”他们的车常年跑在广东二三十度的环境下,工作环境不一样,许多电子元件和电池的工作方法也会有不同。来不及慌张,他开始飞速思考,他们的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。
但去年的梦魇,又一次降临。“3587”这个魔咒一般的报错数字,又一次出现。罗胤龙驾驶着赛车行驶在赛道上,却感知到右后方的轮子不再转动,出现了和去年一样的电控问题。想起上场前电控组的队友们跟他说的,“你使劲跑就好了,跑坏了今晚我来修”。他迅速冷静下来,研判当下的状况,没发现除了右后轮以外的其他问题,他照常操作,顺利冲过了终点,挤进了单圈竞速的全国前三。
胜利是短暂的。耐久赛上,罗胤龙的噩梦成真。他驾驶着车,停在了赛道半途。裁判向他走过来的两分钟内,他还在不断地尝试重新启动赛车,复位电机、下高压,但车一直一动不动地停在原地。裁判靠近车道,告知他,两分钟之内无法重启就只能退赛。直到最后一秒,他都没有放弃,甚至在心中希求能否让裁判帮他按一下后面他摸不到的按钮。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,他只能下车,看着车子被推走。
见证了车队的又一次失败,导演程工却比之前要更期待看到故事的走向。同样,在制片人宋晓晓看来,赢了的表现大多都是相似的:喝彩、兴奋、呐喊,只有从面对输的表现里,才能更清楚地看出这群孩子是什么样性格与底色的人。
赛场外围原本屏息站立的队员们蹲坐在地上,注视着停在中途的赛车,鼻头耸动,有人忍不住落了泪。从赛车上下来的罗胤龙,陷入了紧张过后麻木的空白。身为队长的担当,暂时麻痹了他的失落与难过,他只想着要找齐队伍的人,不能让他们独自在角落里伤心。车队的人聚坐在一起,呆呆地看着车子被推入了库房。
回程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上,罗胤龙遇上一个队员,就和他谈心。在互相的安慰中,沮丧的情绪逐渐平复。
回到学校,罗胤龙没有时间沉浸在失落中,有太多事需要他去做。除了车队的总结大会、队长换届和新队员的培养以外,他还要负责新技术的调研,为车队新的一年铺路。
“成功的时候,就当作一种幸运的眷顾,失败的时候,就当作一种常态,这样无论成败,负担都不会过大。”他已经习惯了快速消化情绪、切换状态。大学几年,他不仅要参与车队的活动,还要兼顾田径队的训练。田径队广东省内比赛成绩一直不错,一到全国赛场,成绩就不如人意。他没有时间一蹶不振,那会耽误车队的进展。
为了今年的比赛,他将出国留学的计划推迟了半年,明年下半年,他将奔赴德国。那里有全球顶尖的车队,他打算进一步学习一些赛车的相关知识。卸任车队队长后,他将用更多的时间做留学的准备工作。但像每一任离开后仍心系广工车队的师兄们一样,他仍会在需要的时候,出现在车队的工作室。
如同去年失败之后鼓着一股劲想要在今年翻盘一样,罗胤龙开始期待明年。他永远在奔赴下一个赛场,像一颗被坚硬的石头挡住的种子,没有发芽,却始终涌动着向上突围的生机与活力。
不是只有成功才是向上。早在拍摄开始前BOB综合体育,程工就在与朱乐贤的对话中袒露了他对“向上”的理解,缩着忍着是向上,倒退一步也是向上,扛过去了也是向上,活着每一天都是向上。
“现在我有些悲伤,眼泪却开始躲藏,内心失去希望,我变得越来越迷茫,是否应该认清现实,我也许就是颗石子,平平淡淡度过我这一辈子……”身边的朋友们身上点缀着斑斓的颜色,他们是花、是树,而穿着灰绿色连体衣的小男孩站在舞台中央,大声唱着一颗不发芽的种子的心声。不远处,孩子们和家长们围坐在一起,欣赏着这场由孩子演绎的音乐剧。
42岁的音乐剧导演陆敏坐在露台上,这里能够看清舞台效果和观众的反应。她发现,在剧目刚开演时,还忍不住点亮手机的几位家长,到剧情高潮时再未将手机掏出来。唱完这段歌词,小演员转过身去,看着男孩的背影,陆敏没忍住眼泪。
孩子们的处境让她难过。听着歌词,她想起小演员们为了演出,早上7点就来剧场报道。他们聚在后台,谈论起自己前一晚还没来得及完成的作业,等演出结束,明天还要继续写,“能不能让我们休息一天?”小小年纪,他们承受着父母和社会传导给他们的成就压力,时间全部被填满。
一颗不发芽的种子的故事,源于陆敏对当下教育理念的思考。儿童剧团周末排练时,陆敏作为三个女儿的母亲,也常和其他家长聚在一起聊天。去年,她遇到过一位母亲,她为了孩子辞掉工作,认为自己已经为此付出了如此多的精力和代价,她的孩子不可以不优秀,她应该考取名校,各方面都应该比其他孩子强。陆敏当即反驳,孩子不是只有一个成长的可能性,孩子本身是他自己,是一个人,不是一件物品。
恰巧法国设计师玛塔莉·卡赛特要在上海办一个亲子装置展,邀请陆敏创作一台配套的原创音乐剧。看着装置展中的种子、蚯蚓和菌菇群落,陆敏一下就想到了种子的故事。所有人都觉得种子肯定要发芽,那如果有一颗不发芽的种子,它会怎么办?沿着这个思路,她和团队想到了这颗不发芽的种子——希德的故事。
陆敏曾坐在观众席里,观察小朋友和家长的反应。一个小时的戏,有孩子前50分钟都在焦虑,不停地问爸爸妈妈:“种子为什么还不发芽?”
等到演出结束,她都要向家长们说,一个孩子不应该为种子发不发芽而焦虑,这不是他应该焦虑的事情,他们的焦虑来自于家长的言传身教,家长的焦虑被他们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,所以才会在一颗种子没有按照既定路线走的时候,产生焦虑。
种子可不可以不发芽,这个问题也触动了有一个女儿的朱乐贤。他看着屏幕里站在聚光灯下的希德,看着他逐渐意识到,即使不能发芽,不能长成一棵树或者一朵花,他仍旧是他自己。朱乐贤开始思考,究竟应该如何评判孩子的成败,如何使自己的女儿健康地长大。
早在十几岁时,陆敏也在身边环境的裹挟下漫无目的地向前跑。初中时,不管是父母,还是老师,都在强调学习成绩的重要性。她没想好以后要做什么,却还是努力地学习,按部就班地演绎着大多数普通人的剧本。为了追求更高的成绩,她将自己学到胃出血。
努力不一定有回报。初三时,陆敏生了一场病,落下了学习进度,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。15岁,她就离开兰州,到上海一所中专读书。父母只付生活费,中专的学业要清闲些,她就到周边的餐馆打工,赚取学费。从十五岁开始自力更生,生存压力下,她渐渐从成就框架下跳脱出来,“我不要发芽了,我只要活着就好。”
活着的欲望,也一度磨灭。2018年,陆敏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。即使是从十五岁开始就习惯自己解决问题,她也难以应对同时看顾两个婴儿带来的身心压力。从怀孕中后期开始,陆敏就睡得不好,孩子生下来后,每四个小时要喂一次奶,更是没有了睡觉的时间。体内的激素由孕时的峰值直接跌至最低点,剖腹产的伤口周边有3年的时间,每到下雨就会疼痛发痒。糟糕的身心状态下,陆敏患上了产后抑郁。
她不敢站在镜子前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她总觉得有两个人在耳边说话。一个在左边说:“都是小事,挺挺就过去了。”另一个在右耳边反驳:“别听她的,这种日子没完没了。”严重的时候,陆敏还有自残的倾向。在某天凌晨三四点,她想要结束这一切,这一生的过往在她眼前闪回,她开始脑补自己逝世后的事情。想到自己的女儿,不想影响她们一生,也不舍得带她们一起走,她改变了主意,对自己说:“请你坚强。”
很长的时间里,陆敏都是自己带两个女儿,她戏称自己为“长了11个脑袋的妈妈”。每天她要早早醒来,给两个女儿洗漱、准备早餐。遇上周末排练,就开车带着她们一起去剧团。每晚,她要给她们讲不同的睡前故事BOB综合体育。她们入睡前,陆敏是很难专心工作的,女儿们叫“妈妈”的声音总从家里的四面八方传来。今年11月的演出前,陆敏常常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。
她很瘦,脸上没什么肉,棱角锋利。细瘦的身躯上,却能挂住两个女儿的重量。同时将两个女儿抱在臂弯时,她分不出心思注意身体上的感受,只想着怎么将她们稳稳托住。
从孩子们身上获取了生的力量,陆敏也想让孩子们拥有更多彩、更有活力的人生。她始终记得剧团孩子们告诉她的,“不要觉得孩子们什么都不懂。”她和两个女儿平等地交流,教会女儿们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,如何反驳大人的话,做一颗有自我、不害怕长大的种子。坚守住自我,才能跳出他人目光的审判,找到属于自己的向上路径,勇敢、坚定地书写自己的人生剧本。
陆敏并不指望来看戏的孩子和家长,当下就能有所改变。这出戏剧,也许也是一颗种子,播种在人们心里。每一个走出剧场时还在哼唱某句歌词的观众,在未来人生中的某一时刻,可能会突然想起:希德是可以不发芽的,希德是一颗被埋在土地里的莲花的种子。
无论种子发不发芽,它都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长。纪录片《向上》中另外6位主人公身上,同样有多样的生活姿态:大学毕业后回归乡村的孔博,坚信都市型农产品可以冲出困局,一股脑扎根在土地上。抱着拯救生命的信念,王书浩穿行在各大医院推行自己的模型,他笑着将自己的热情投入到人类健康事业中。喜欢“多管闲事”的葛凌宇想让青年人感受到“被看见”的关怀,改变他们眼中的空洞与困惑。B站百大up主“盗月社食遇记”的创立者杨树梢,和同伴们一起从无到有,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传递着他们的力量。独自带女儿十年的朱胜男,陪伴女儿成长的同时,也在实现自我成长,期待着和女儿一起迎接人生的新课题。
12月24日,腾讯视频与蔚来联合出品的用户故事纪录片《向上》,全片已在腾讯视频上线,邀请大家年末一同感受多元人生,为开启新的一年积攒能量与勇气。